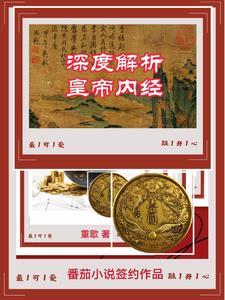书画村>西北偏北电影简介 > 第83章(第2页)
第83章(第2页)
其实当年她也偷偷许了一个愿,希望能安居在河流交汇的地方。
酒过三巡,不知怎地谈起了家长里短,文思月句句话里都是羡慕她的意思:“哎,只有结了婚才知道,女人光是赚钱还不够,还得回了家轮番伺候老中小,就算是忙了一天累瘫床上,还得起来帮闺女遛狗。”
她说要有重来一次的机会,也要远走高飞,要去华尔街闯出一番天地。
人就是这样,没有什么就偏偏想要什么。
姚希将酒杯满上,抿了一小口:“行啦,别得了便宜还卖乖,好歹你醉了有人接你回去,我就算到了家,也只有马桶陪着我。”
她们发出咯吱咯吱
的笑,像是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儿,滔滔不绝、直言不讳地互诉衷肠。
“他一个离异带娃的人,竟然问我三十岁还没谈恋爱,一定是处女吧?”
“你说什么了?”
“我问他和前妻离婚,难道是因为不是处女了吗。”
文思月拍着大腿笑出了眼泪,姚希也是酒酣耳热的,一来一回不知聊到了几点。
他们住的地方离小酒馆不远,文思月喝得有些断片,是姚希和她老公两人把她架回的住处。
文思月老公十分客气地问她需不需要被送回去,她是个讲分寸的人,觉得不大好,便一口回绝了。
孩子很是听话懂事,一口一个妈妈叫得人心里暖暖的,还洗了一块热毛巾搭到文思月的额头上。
转过来又对姚希道:“阿姨,你不头晕、恶心、想吐吗?”
她其实眼前已经出现了重影。
“不呀。”
—
这里的公交末班车在十点,姚希十分幸运地赶上了。
车里只有两三乘客,她坐到了最后的位子,费力拉开了窗户,想吹一吹酒气。
大概是司机也想要快点下班,车子开得不稳时慢时快,还以为是在走什么乡间土路。
姚希被晃得有些恶心,索性把眼睛闭上,不再看外面。
浅眠时做了些梦,都是稀碎的片段,连不成什么剧情。
中间大约停了几站,她没有听见播报声,再睁开眼时车厢里独独剩下了自己。
上衣口袋震动了几下,姚希拿出手机,看到了一条远从新西兰传来的国际漫游信息。
——希姐,明天是圣诞节,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
回国后她换了个号码,只告诉给了gwen。
姚希抵住胀痛的太阳穴,正在想要回信的时候,瞥见窗外于黑夜中拔地而起的,由一块块石头堆叠而成的万重山。
她恍然回忆起梦的内容,是她变成了一棵大树,每当风拂过,就有叶子从身上窸窸窣窣地掉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