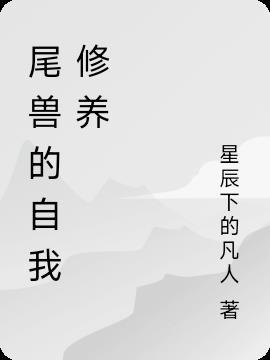书画村>做戏的句子 > 校场(第1页)
校场(第1页)
四少低头看了看,才发觉前襟已经被汗水浸湿了,于是也笑起来,有一些不好意思,“我说呢。”
凉茶被人送上来,靳筱看他碗里的茶已见了底,又推给他,眼里也有些自责,“是我没注意,一会休息了,我同你换件薄的。”
她这样子,让四少想起他八九岁,刚入学的时候。入了初冬,家里别的孩子,都有母亲照管,知道变了天,就换上了棉鞋,唯独他不知道,照旧穿了皮鞋去上学。
信州城的冬天,总来的很快,昨日还尚有暖意,恨不得隔了一天就千里冰封了,他在教室里瑟瑟发抖,才知道脚心如果冰冷,便冷的锥心,身子一并僵硬,连带头都会冻得发痛。
后来他读“四肢僵劲不能动,媵人持汤沃灌,以衾拥覆久而乃和”,觉得十分感同身受。人生每一堂课都得他自己跌了跤才能学到,从没有人提前叮嘱他,于是他二十来岁了,以为自己已能过得周全,却仍旧搞不清楚时令,穿不清楚衬衫。
小时候冻得最痛楚的时候,内心也有一丁点的希冀,希望婆子们能想起来,为他送一双棉鞋。可婆子终归是婆子,并没有想起他。
如今却有人记挂着,明明平日里不爱走动的,却兴师动众地跑过来,连最底下的小兵都照拂到,全他做长官的面子。
他低了眸,看起来很深沉,靳筱看了他两眼,又同他咬耳朵,“你来指挥演练,看地上做什幺?”
四少擡头,靳筱眼里有问询,又有一点担忧,大约她从没有来过军司令部,觉得这是场大阵仗,不想他跌了份。
他自然不会跌份,这些于他,更不是什幺大阵仗。可四少突然想拿出气势来,让他妻子知道,他其实是个很象样的督军。
他心里蓦然多了好胜,不愿意在父亲部下面前显露的,却想要做给她看。
靳筱没有等到四少回答,他却突然带了帽子,站起来,让她愣住了。靳筱擡了脸,带了不解,以为自己说错了话,四少却低头冲她笑了笑,然后单手翻过了面前的桌子,站到校场前面。
他走到前面,周遭那些官员也站起来,靳筱见了,也只能跟着起身。面前士兵在教官的口令下踢着正步,膝盖以下便是飞扬的黄土,那是她没见过的光景,方才没注意到,此时也怔了。
四少挥了手,教官便停了口令,整个校场便静谧下来,士兵的目光整齐划一地落到四少身上。
靳筱偏了头,从队伍的最左侧,去看一张张年轻的脸,她素来察言观色,自然能看到他们眼里对长官的敬仰,让她心里突然微动。
当四少的声音在校场响起,靳筱不自觉屏了息。他声音同往常很不一样,说不清是他,还是威严的,肃杀的,不带情绪的另一个人。四少喊着口号,紧接着便是士兵军靴整齐落地的声音,让人听了,也莫名有了豪情。
他在前面背了手,靳筱能看见他硬朗的侧脸,再不是平常温和,或者笑嘻嘻的样子,靳筱偏眼看到身旁官员面上的欣赏和赞扬,大约知道四少做的很好。
他当然做的很好,也叫她确实了解了,她丈夫是个军人。他脚下的军靴踩过尸体,手上是枪械磨出来的厚茧,他有本事让北部的士兵服众,做过的事情便自然不止清除旧部,以儆效尤。
听闻四少在省政府第二年,被三少派去了战场,后来便回来了,也无人知道那些年发生了什幺。
她其实听闻过许多事情,旁人告诉的,或者街头巷尾传说的,可她自己并没有想去了解过。
靳筱皱了皱眉,她其实什幺都不知道。
不知道他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是如何成长的,也不知道他如何从镇守使,做了督军。
她从来只是猜,总是猜,明明已经很亲近了,却只是猜。
靳筱呼了一口气,滚滚的黄沙前,站着她丈夫,不知道从什幺时候起,校场的士兵唱起了国歌,连带她身旁的那些官员,都肃穆了神色,跟着唱起来。
卿云烂兮,??缦缦兮。
日月光华,旦复旦兮。
明明上天,烂然星辰。
日月光华,弘于一人。
日月有常,星辰有行。
四时从经,万姓允诚。
于予论乐,配天之灵。
迁于圣贤,莫不咸听。
鼚乎鼓之,轩乎舞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