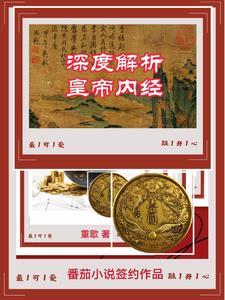书画村>凌海市人民医院120电话 > 第7章(第1页)
第7章(第1页)
远山的青影与碧空界限模糊,是这座小城的背景色。
时婕舒展双臂,老家熟悉的气息裹在风中,扑面而至,呼啸着穿过她的身体。
比起北京,这座小城像是被封进了时光的琥珀,寻不得日新月异的发展,却凭年年如是的确定感令人安心。
栏杆上停落的麻雀被这不速之客惊扰,扑棱棱飞去了另一座楼顶,立在制高点俯瞰,好像它们也拥有这城市。
时婕各种找角度,自拍了好些照片,挑出几张发朋友圈,又专门发给林桃。林桃大为羡慕,说感受到了“自由的味道”。
她翻着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,上扬的嘴角却突然凝住——那里面竟有前男友徐维。
手机震了下,徐维发来的微信。
「你回雁留了?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?」
时婕撇撇嘴,「分都分了,说也多余。」
过了几分钟,那边才回复,「小婕,咱俩认识快十年了,就算分手,我也当t你是朋友,我希望你好,真的。」
还来煽什么情?时婕腹诽,眼眶却有点湿意,「那你怎么样,不会都交上新女友了吧?」
“对方正在输入”断断续续闪了好一会儿,「父母给介绍了一个,接触有段时间了,双方家长都见过了,可能明年结婚吧。」
本来就是句调侃,没想到竟然命中,她心中酸涩,还是装出风轻云淡往事如烟的气度体面回复,「挺好,祝福你。」
「还好没被阿姨吓出毛病来(笑哭表情)其实要不是因为阿姨,咱俩……」
这条消息刚弹出来,也就两秒后,被撤回了。
她莫名想起去年520,徐维说“我喜欢你”时真挚的眼睛。
分手才几个月,他不仅找到新女友,甚至都到了计划结婚的程度。那她算什么呢?
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,而她就是失败。所谓吃一堑长一智,她就是那个堑。堑,大坑也,壕沟也。
两个人,腻歪的时候,还以为自己是对方心头的独一无二,结束时才发现,原来不过像银行柜台走一趟,屁股刚从凳子上挪开,就听见叫号机在喊“下一位”。
什么独一无二?荷尔蒙上头的病症罢了,轻症自作多情,重症耳聋眼瞎。
时婕找了个背风的方向,席地而坐,靠着用途不明的石墩子。把手机搁到旁边地上,任由它嗡嗡作响,不再理会。
最初发现这天台时,她就想,这么开阔的好地儿,不支个炉子搞搞烧烤简直暴殄天物。时婕想象着滋滋冒油的五花肉,咽了咽口水,又拾起手机,在外卖平台上点了一堆烤串、三听啤酒跟一瓶江小白。
等外卖的时候,她瞄到旮旯里塞了个正正方方的东西,被好几层塑料袋包裹得挺严实,掂在手上沉甸甸。
她压制不住好奇心,小心翼翼拆开来,原来是套花花绿绿的少年漫跟一相册的奥特曼卡牌,估计是哪家小学生不能为家长所知的秘密宝藏。
时婕坏心眼地猜测,要是这孩子上来探望这藏宝地时发现东西竟然不翼而飞,不得嚎成什么样,她想想都觉得十分着笑,不禁蹲在地上嘿嘿地乐了一阵,然后掸掉塑料袋上的残雪,把东西照原样包好,牢实塞了回去。
外卖送到了,时婕盘着腿喝酒撸串,吃得满嘴油香,三听啤酒下肚,最后去开江小白,就见包装上写了句:
「爱情这种事太极端,要么一生,要么陌生。」
她眯着眼看了会儿,哼了声,“矫情。”
顺手把那包装一扯,搓成个团儿塞进空啤酒罐,然后一口干掉半瓶江小白。
吃完喝完,时婕便呆望着傍晚的日落。
太阳渐渐下坠,光芒却越发盛大,将半片天空染成橘子汽水般明艳的色彩。不过须臾,落日沉没,仿佛橘子汽水里坠入了一滴深蓝色的墨,摇匀了混成温柔的紫。随着墨汁一滴又一滴落进去,天色于是乌压压地彻底沉寂了。
底下渐渐热闹起来,应该是楼里的人陆续到家了。时婕坐得尾巴骨发疼,索性仰面朝天瘫成个“大”字。
不知道哪一户传出小两口的嬉笑声、铛铛的剁菜声、菜入锅时的刺啦声……一浪浪地往她耳朵眼里涌。
时婕抽着鼻子小狗似的嗅着菜香,一边扑棱蛾子似的扑腾着舒展胳膊腿儿,可着心意撒欢儿。
然后雪下起来了,雪花漫天,混进风里,打着旋儿落到她的脸庞和散开的发丝上。
她安静欣赏了会儿,撑着胳膊把自己支起来,收拾干净一地空瓶空罐,起身时脚有点软,像是踩在云里。
她便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踩了一路的云,一阶阶地下楼去。
总算到了五楼,她正要摸钥匙开门,突然撞上个什么东西,手里那兜子瓶瓶罐罐被撞得叮当乱响,楼道里的声控灯随之亮起来。
男人身上还带着微凉的雪气,待到看清她,“……你?”
时婕倚着墙站着,立起右脚的鞋跟抵住墙根,缓缓露出个笑,“哦,邻居……你好哇,邻居。”
江承不应,只微皱着眉看她。
时婕比比身后,“这间房,我租了。”
他点头,转身开了门要进去,却被时婕拽住衣角。
“我……忘带钥匙了……”
他的目光审视地看进她的双眼,像是在判断这话是真是假,接着扫了眼她的手,“手机带了?”
“……嗯。”
“打给开锁公司。”
眼看门就要关了,她急起来,“你就忍心看我蹲楼道里等?下雪了,好冷的!”
逐渐闭合的门缝迟疑了几秒,而后慢慢扩大,透出暗黄色的光,比头顶的白炽灯惨白的光线舒适得多,令人产生一些关于诸如温暖一类的联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