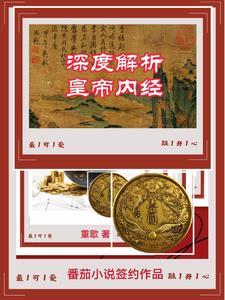书画村>道狭草木长古诗 > 第46章(第1页)
第46章(第1页)
国共内战已近十年,经历张少帅的兵谏,形势虽较四一二那会缓和许多,却依旧不容乐观。他听闻三哥儿此番是要潜伏在北平,前途未卜,只得将小少爷安排给他。小少爷在南京,在国民政府下辖的军校,就在反动派的眼皮底下。老子若是暴露了,就得靠宋希微把那孩子捞出来。
门庭那有人过来,步子轻缓,若不细听,还以为是雨声纷繁。
李晏辞谢了引路的老妈子,未进书房,撩开屏帘探出小半张脸。那脸孔像极三哥儿艳绝的夫人,眼角亦有颗朱砂痣,却不显媚态,丝毫不近人间烟火。
“先生。”他轻唤了一声,“阿晏贸贸然来,惊动了。不过是避避着外边的凄风苦雨黄梅节色大半,可惜留不住春,怎般轻愁都是无可奈何了。”
他念的是唱词。
宋希微一顿,搁下笔,示意他到身侧来。李晏走过去,将背后的小三弦解下,扣在怀中。
外三门家个个都是军校出身,唱弹词不过是老人传下来的老营生。李晏在南京军校修学,得空时也回吴江,去光裕社坐台,唱《秋海棠》,一开嗓便逼得人掉眼泪。这曲子李家老爷子常唱,戒人莫要入戏词太深。也因此,李家小辈没几个将弹词当作正经吃饭家伙。
宋希微存心逗李晏,将他腕子拉过来,笑道:“这双手倒是像你父亲,握书卷好看,捻这伶仃三弦也好看。殊不知拿枪时,可有他那般好看?”
“今年便拿枪。”少年垂下眸,“必然比他好看。”
李晏十九岁。
宋希微十九岁这会初到巴黎,那是近十年前的事了。他见过塞纳河上鱼鳞云涂抹的长空,闻过东去的故乡的流风,读过果戈理、叶赛宁和马克思。离开之后,他宁可花尽余生去寻回欧罗巴的彩色和铁窗外的朝霞,但相比于生在动乱里的李晏,他简直幸运太甚。
“好小子。”他道。
次日过礼拜,李晏回了军校,那把三弦被落在宋家。宋希微见惯了西洋乐器,拨弄几下也不得法,就让它在屋角哑着,自己回中央大学讲了半天的古代文学史。
日色沉下去,他便往学校隔壁的茶馆里一钻,带了报纸和书籍,要了壶正山。阁楼下评弹的唱起来了,都是女子,声音软腻得很,颠来倒去地呢喃钱塘潮、吴山桂与温柔乡,勾着人魂魄至苏杭。
也不知李晏现在开口是什么光景。
“还在看李大钊啊。”院里的老头儿陈撇拎着旧布包和一沓书纸坐到他对面,“他的那篇马克思主义观也是老鞋皮头了,翻出来嚼干嘛?”
“他说‘现在理论’是经济论,我觉得不错。”宋希微道,“老教授,什么都得进步,你得承认吧?个人经济主义总会落后,你得承认吧”
旁边桌两个人瞟过来。
“小点声。”陈撇一咂嘴,宋希微轻咳了几声,将眼睛摘下。下边一曲唱罢,换上满庭芳,先上一段了一段琵琶击弦,将陈撇余下的话打得断断续续:“少多嘴,咱就安分点教书。这冷战不知战到几时,满大街都是特务,提共产就是找枪子儿吃。离了象牙塔,不好安生啊。”
苍头白日,还能吃人不成。
两人不做声地拾起报纸来看,在大堆粉脂烟草广告与婚讯启事里挑拣有意义的字句。外边天色阴下来,评弹台上新换的女师傅唱慢了半拍,宋希微刁钻地啧一声,回过身去,就见门堂处跌撞进来一个人。
那人浑身褴褛衣衫,拎着把破伞,宋希微一眼就认出是苏五爷。这老头消息灵通,今日秦淮旁哪位招牌跟军官跑了,庐山发来几个急电,他都清楚得很。别人当他是个跑马的,只有宋希微知道,这家伙是个正经军官。
苏五爷瞧见宋希微,过来一把扯住他的袖子,希微还当他鸦片瘾头又上来了,就听他啜嚅道:“司令家的,我可找着你了!出事儿了,他娘的出事了……”
“什么,什么?”
弹评弹的停了下来。众人站起身,向他望去。只听他装疯卖傻般喊道:“日本鬼子过了卢沟桥,将宛平城给轰了——诸君,北平北平要沦陷了!”
耳边唯余闷雷翻滚低啸。
三弦(2)
“全中国的同胞们,平津危急!华北危急!中华民族危急!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,才是我们的出路”
李晏将军服换作青衫,把白纸铅字裁做条卷。那是北平卢沟桥的消息与中共组织的呼告指令,要被带出反动者的封锁,叫各大报社刊出来。他与父亲做这行当几年,现在父亲身在北平,自然是他继续拉着线头。
他在去年秘密宣誓入党。
外边一阵匆忙脚步声,宿舍门被人大力地拉开,他旋即将余下的字纸揉进手心,回身见夏庆年大汗淋漓地出操回来了。
“你听说没——北平那出事了,但消息给封死了。”他将衬衫解开两颗扣子,“你父亲不是在北平有差事吗,你不问问他怎样了?”
“他不过是后勤的,知道甚么。”李晏未答他,寡淡地将话头拽到自己这,“下午我跑出去一趟,替我向五爷告个假——说我探病去了。我那把老三弦,你扔哪去了?”
“行嘞,帮你和苏盛说道去。你最近都跟偷鸡似的。”夏庆年拿了角凳,站上去,在柜顶将那积满灰的长颈儿取下,“要什么老三弦,你不是打了把新的”
“丢了。”李晏一顿,将三弦扯来,旋身出了门。
长廊空寂,烫金的门牌号拉扯锈迹与阴影。李晏将字条按进三弦包被蟒蛇皮的琴箱里边,提着青衫摆儿,掀开一旁窗子。这窗本是被糊上的,他找了个日子将上边的石灰粉敲开,也没人发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