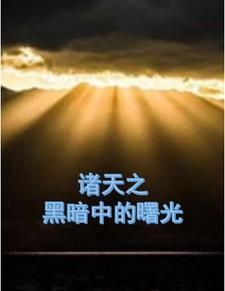书画村>月光不沉沦by零下八度讲的什么 > 第61章(第1页)
第61章(第1页)
来年春季,姜仪再一次踏上飞往意大利的飞机。
他扮演了一个足够令人生厌的疯子。没人比他更懂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,姜仪感觉自己分裂开去,他想要落泪。
说出那句“我永远不会放过你”的时候,姜仪努力回想,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?
真真假假的,有谁能分得清。那才是真实的,他压抑的自己,也许。姜仪自己也不懂,祈云转身的那一秒,他到底想要听到什么回答。
如果祈云选择上来抱抱他,他还能放过吗?
不过现实没有如果,姜仪也不是个合适的爱人。他对祈云的感情从不纯粹,他没资格做出这些念想,左右再无交集,爱和恨也没有太大差别。总比相安无事地忘记好上许多。
祈云选择背道而驰,这符合姜仪的目的。
他说了许多恨,也是真的恨了。所以姜仪怎么能不算成功,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,他都成功地算计了所有。
——“不认识。”
姜仪骤然睁开眼,整个人从深陷的回忆里抽身而出。他深深喘了口气,犹如迟来的梦魇,活活要将他溺毙。
太无趣了,他放下晃动的酒杯,很随意地扔出去。
装着红酒的杯子摔在大理石地面,发出尖锐难听的响。液体汩汩四散,流淌在地面,姜仪盘腿坐起来,看不出悲喜。
太难受了,他太难受了。他执着了这么多年的东西,真正把握到手里的时候,姜震云亲手被他送去精神病院的时候,他都一点儿不快乐。
他只感到无趣,原来得到,也是这样痛苦的。
姜仪裸足踩上摔的破碎的酒杯碎片,感受尖锐从脚掌蔓延去刺痛,才终于压抑下胸口震动的闷痛。
不该学什么狗屁意大利语的,还不如听不懂呢。
不认识……他嗤笑一声,去他妈的不认识。姜仪张开双手,任由身子向身后的沙发倒去,后脑勺撞到哪片柔软,弥漫开点疼。
他翻了个身,全然不管脚掌上的鲜血淋漓,摸到扔在一旁的手机,像得到了什么心爱的玩具,笑眼盈盈地,拨通了那串早已熟记于心的电话号码。
“喂?”
铃声响了一会儿才被接通,alpha兴许是在睡觉,嗓音还带着梦中的哑:“你是?”
“你猜一下。”姜仪低着头,额前的碎发挡住眼睛,看不清神色。有点痒,也疼,他抬手揉了一下,才笑着接上后半句:“真的认不出来吗?祈云。”
“我们今晚才见过的,”他不自觉缩了下脖子,这时候后知后觉地感到冷,也感到流血的疼了:“我是依依啊。”
祈云吸了口气,“……姜仪。”
“好嘛,你又生气了。”姜仪笑了,声音低下去。他换了只手,两只手一起捧着,尖瘦的下巴搁在膝盖上:“别生气,我挂了。”
他没再犹豫,说挂就挂。
他们才没有不认识,姜仪曲了下身子。他反驳道,祈云都叫的出他的名字,怎么可能不认识。
◇“恨。”
漆黑的夜幕,只余空调运作同电话被挂断的声响。哦,祈云慢半拍地想,电话挂断只有一声。
多出来的,都不过是他自己,在这个称得上孤寂的夜里,无端生出的错觉。
那是战栗,alpha闭了闭眼,无声吐出口浊气。就算主观上并不像承认,祈云也不得不认清这个事实,他的确忘不掉。
甚至不止是忘不掉。
更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,就像现在,祈云无法再次入睡。他犹如陷入极端的平静很久,连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一点,却在隔了很久之后,骤然被惊起巨大的波澜。
姜仪举着酒杯,坦然自若朝自己走来的那刻,生理性要泛出的反胃,在瞬间席卷了祈云的整个大脑。
他轻而易举地感到痛苦,光是看见姜仪熟悉的身影,和听到一句简单的声音。
在自以为早已放下,能全然做到坦然面对以后。
祈云很久没有回过江城,往昔的记忆,也一同随着时间掩盖,变得不再清晰。
大部分清醒的时候,祈云并不会想起有关这里的一切。在那次堪称爆发的争吵以后,祈云第一次很有些任性地做出不算理智的举动。
他请了很长时间的假,把自己关起来,度过了漫长的,全然与外界失联的生活。
而在此之前,祈云还维持着最基本的平静,在起伏的胸口缓过来之后,朝方知宇挤出了个笑:“让你见笑了。”
“不用担心,我没事。”
祈云沉默少时,在方知宇欲言又止的担忧神色里,轻声选择了安抚。
他的确看上去不在意,仿佛刚刚那个在风雪中红着眼眶同人争吵的alpha不是自己。丝毫不被情绪左右似的,甚至可以出色地处理完堆积的公务,将一切繁杂琐碎都处理妥当,才提出需要休息一段时间的请求。
方知宇不会忘记,再一次见到祈云,是在半个月之后。
他没太大变化,没有如想象般变得狼狈,也没有瘦的不成人样,甚至气色红润些许,比起失恋后的自我调理,反倒像是真的趁这段时间给自己放了假。
谁都察觉不到,或许连他自己都察觉不到。
但切切实实的,祈云靠着床头,感受心脏的剧烈跳动。他想,事实上,他很难再睡上一个好觉了。
枯坐时的时间流逝格外快,天边泛起鱼肚白。alpha缓慢地眨了下干涩的眼,在生理性眼泪从眼眶坠落之后,才终于迟钝地从床上起身。
他想起决定回国前的最后一晚,金发碧眼的医生正有些严肃地坐在他面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