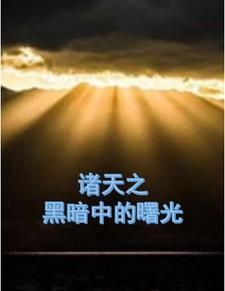书画村>朝阳路上的医院 > 第98章(第1页)
第98章(第1页)
“虽然很残酷,但是是这样的。”亦柔平静道。
“女性即便作为实际上的生育主体,在男权社会的规训下,这种生育主体的地位还是会被让渡给男性。”
“所以就能解释,大多数男同出柜的时候,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他家无法传宗接代,能够解决这个问题,那其他的就不是问题。”
“但如果是女同出柜,就会默认一下子失去两个实际上的生育主体,为了维护男权社会规则不崩塌,直接否认女同的存在,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。”
她的这段话让我冷静下来,是啊,不然为什么几千年的历史,却很少找到女同的痕迹呢。
看了眼旁边坐着的人,突然就释怀了,不管是自然筛选还是社会规训,都无法阻挡我们相爱。
*
亦柔家住在老城区的政府家属楼里,虽然小区设施已经有些陈旧,也算闹中取静,胜在地段好,去哪都很方便。
老式的声控灯得使劲跺脚才能亮起,门锁有些陈旧,稍稍拧动就发出刺耳又沉重的声音,亦柔还没打开,里面的人听到动静已经出来迎接。
“回来啦,我一直在阳台那眼巴巴望着,看见你们下车就等着给你们开门呢。”
面前的人似曾相识,身穿灰蓝色的兰花针织衫,烫染过的卷发柔顺地披在肩头,更叫人猜不出原本的年纪。
一开口就叫人如沐春风,如同她的名字一样,何淑宁,在那个年代能取这样的名字,家里大概是书香世家。
亦柔的妈妈何淑宁之前曾在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教美术,墙上挂着她画过的油画,笔触有力用色大胆,我虽然没有什么画作赏析能力,却也能感受到画中蓬勃的生命力。
从家里的布置得以窥见主人的品味。
整体简约不简单,陈设布置色彩丰富,却又不会给人杂乱之感,对比刚才满目灰白的筒子楼,步入其中就像是误入森林中的小木屋。
“我妈知道你要来,提前半年开始动工,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遍。”亦柔挨着我小声道。
我有些受宠若惊,乖巧地阿姨长阿姨短地跟何淑宁聊了半天。
趁着亦柔在厨房热菜的功夫,还如愿以偿地看到了亦柔小时候的照片。
九岁之前的她,每一张都笑得很开心,有一张她在我们当地游乐园里拍的照片,我也曾经在同样的地点拍过。
她对着镜头滋水枪,笑得见牙不见眼。
翻着翻着,我突然在亦柔的高中毕业照里发现了误闯入镜头的我。
就在学校的那架紫藤花架下,我们穿着同款白t蓝裤的校服,都梳着马尾辫,亦柔望着远方发呆,被她同学拍了下来,顺带拍下藏在花叶背后偷看她的我。
“阿姨,这张照片我能拿走吗?”
何淑宁拿着照片仔细辨认,惊喜道:“后面那个人是你吧,当然可以,多难得的缘分呀。”
她慈爱地注视着我,身上散发着好闻的洗衣液的芳香,亦柔和她的眉眼很像,更多几分凌厉与不羁,再温柔的时候,也不似她这般柔和。
“小园,谢谢你,和你在一起之后,亦柔真的开心了许多。”她拉着我的手道。
那些错过的少年时光
亦柔妈妈和我妈妈最大的不同,大概就是她真的很善于表达爱。
从进门到现在,已经数不清夸了我多少次。她在不断向我释放信号:你是值得被爱的。
关于何淑宁,小城里也有很多传言。
她是她们那个时代有名的美人,与亦柔的父亲郎才女貌。
人生转折出现在成为烈士家属的那一刻。在外人眼里,何淑宁和亦柔享受了烈士家属的优待,那就应该默认承担受人指点的义务。
亦柔不可以学习不好,不可以与同学起冲突,因为她是烈士的女儿;
何淑宁不可以开心,不可以享受,更不可以改嫁,因为她是烈士的妻子。
在小城里,唾沫星子真的能淹死人。
所以当何淑宁有离开的机会,亦柔坚定地选择站在她那边。
为了能尽快经济独立,不让母亲担心,亦柔才会放弃原本想要报考的导演系,转而走保送给了奖学金的学校。
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亦柔是怎样做出决定的,只记得她曾经说过,她想认识,没有成为她妈妈之前的何淑宁。
仔细观察饭桌上的这对母女,身份像是发生了调转,亦柔更像是母亲的角色,布菜添饭,默默承担起照顾人的任务,何淑宁负责夸夸,给足情绪价值。
她们虽然有很长时间都不在一起生活,却能够适应对方的节奏,母亲由衷感到快乐,女儿才会快乐。
只是太多母亲常常把牺牲、奉献视为爱,有的时候,女儿真诚希望母亲能自私一些,先去爱自己。
我之前还担心过亦柔没有母亲陪伴会在爱上有所缺失,现在看来是太过狭隘。
餐桌上,何淑宁怕冷落我,在享受亦柔照顾的同时,将我照顾得无微不至,只要稍微有所动作,她就会抢先一步帮我做好。
“你坐,我来帮你盛,别烫着。”
何淑宁展现出来的亲切和待人接物的方式吸引我不自觉想要亲近,人在过渡兴奋时,说话都有点不过脑子。
当她递来汤碗时,我脱口而出:“谢谢妈。”
没给我尴尬的时间,何淑宁迅速应了声:“唉。”声音清脆,有点、可爱。
那双弯起的眼睛几乎在我进门后就没有放下过,眼角的纹路最明显,是笑意留下的痕迹,是被爱意滋养的花朵,我由衷感叹,那是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