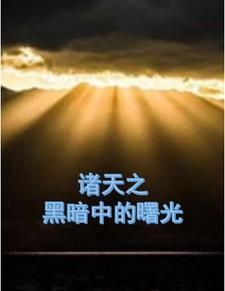书画村>和离后前夫失忆了免费阅读 > 第76章 疑乱(第1页)
第76章 疑乱(第1页)
修竹院内一地的狼藉,各种瓷器碎片散落一地。
“郡主,您可不能再砸了,动气伤身……”
碧池在一旁一边装模做样地劝着,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下跪着的追月。
自从这追月自以为得了苏怡言的把柄,用这把柄到郡主面前邀功,每次来修竹院都在她面前得意得不行,不是令她沏茶看座,就是使唤她做这做那,那副高人一等的姿态早就让她看不惯了。
真把自己当姨娘了么?
笑话,就算郡主将来要为长公子纳妾,那也是她碧池,有她追月什么份?
“我怎么能不动气?”
柳月眠气得差点咬碎了后槽牙,手中的帕子都快绞断了,恶狠狠地瞪着追月:“说!你是不是故意的?是不是你与苏怡言合伙起来故意害我丢丑?别忘了你哥哥的命还在我手中……”
“不是的,郡主,此事我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,我也不知道为何长公子会在飞霜院……”追月瑟瑟抖,不停地磕头表忠心,直到额头红了一片。
“行了,别在脸上弄出伤。这次就先断了你那哥哥一只手,若有下次……”
“郡主开恩,我哥哥是家中唯一的男丁,若断了手以后不好娶上媳妇,家中香火就断了,要罚您就罚我吧……”
追月慌了,连忙抱着柳月眠的腿连连求饶。
柳月眠一脸嫌弃地将她一脚踢开。
这种贱民人家的香火断了便断了,有什么要紧的?
这一脚恰好踢到心口,追月顿时半晕了过去。
“郡主,您若要罚这贱婢,让老奴来就行,哪里用得着您亲自动手?动气伤身,您也要为小公子想一想,别连累了小公子的身体。”
“你们都在心疼他的身子,有谁心疼我?若不是这该死的蛊毒,我哪里用得着受制于人……”
模模糊糊中,追月听到了两人的对话,觉得有些奇怪,还未来得及细想,便彻底晕了过去。
……
苏怡言本以为“捉奸”一事结束,谢淮会重新回到修竹院,如同前阵子一般陪着哄着柳月眠母子。
但之后谢淮依旧日日都来飞霜院,一有空就陪在她身旁。
修竹院那边的戏码每日照常上演,可却再也叫不走他,甚至好几次,容嬷嬷都被直接拦在了飞霜院院外,连进都进不来。
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这是将修竹院那边冷着了。
苏怡言有些恍惚,一切似乎回到了从前,准确的说应该是更甚从前。
飞霜院中的下人们个个红光满面,走路带风,私下里都议论着,之前那些喊着要走的人眼神不好,谢长公子最在乎的还是谢少夫人,这几日百般照顾,将人当成自己的眼珠子宝贝着,就差日日捧在手心了。
苏怡言仿佛活在了梦中,一个谢淮为她打造的梦境。
每日的吃食都是厨房精心准备的,每一道都刚好符合她的喜好口味,其中不乏前阵子她偷偷从酒楼带回来的菜式。
后来一问才知道,谢淮将人家酒楼的厨子直接挖回了府。
五公主气得在书信里骂骂咧咧:“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吃饱了撑着非要挖我新招的厨子,在店里吃不够,还要把厨子带回去,这人嘴得馋成啥样?”
苏怡言心虚得不敢回信,默默又吃下一块炸鸡。
前阵子谢淮在朝中得到了皇帝的夸赞,宫中下来的那些赏赐,最金贵的那批都是先送到了苏怡言这里,任她挑选。
那独一份的蜀锦,更是连谢老夫人和谢侯夫人的手都没经过,就直接送到了飞霜院。谢淮让人替她量身,连夜将那蜀锦赶制成罗裙……
苏怡言咳嗽一声,谢淮会将茶水喂到嘴边。
她皱一皱眉头,谢淮就会问她哪里不舒服。
苏怡言想笑,却笑不出来。她最需要他的时候,他不在。
如今,她已经不需要他了。
陆然医术极其高明,那一夜用针加上之后几日的汤药调理,早已经将她的病治好。就连腿上那道很深的伤口都已经愈合了,只是留了道疤。
谢淮从宫中御医那求来了上好的去疤药,每日坚持替她涂药。
“痕迹淡了些。”谢淮握住她的脚踝仔细涂药,她小腿上那道淡粉色的疤痕在白瓷般的肌肤上十分显眼。
苏怡言无所谓,留疤就留疤,好让她记住自己是死过一次的人。
看着眼前低头为自己涂药的人,苏怡言心平气和地同他说:“我的病早已痊愈,夫君该去陪一陪怀佑了。”
谢淮手中动作没停,头也没抬一下:“夫人若不喜欢,我便不去。”
随着药膏被慢慢抹匀,淡淡的药香在室内弥漫开,清凉中带着一丝苦味。
苏怡言有片刻的怔愣。
他不是一向最宝贝他的那个孩子么?
她还记得当初在宫中,他是怎样焦急地抱着那个孩子匆匆离去;那孩子只是磕破了一点皮,谢淮就为了他迁怒了整个院子的下人;那日一起逛街市时,只要是那孩子想要的,他都一一为其买下,眼中是满满的疼爱之色……